
徐梁潤兒老師的訪問

(記:小記者,徐太:徐梁潤兒老師)
記:那年加入聖芳濟各任教?
徐太:與聖芳濟各同步成長,在我出道的第一年就在聖芳濟各任教,這年也是聖芳濟各開校的一年。學校的開始也可算是我教學生涯的開始,即是1977年。
記:為何會加入這間學校?
徐太:其實在我這個年代,搵工做並非易事,而有學校聘用自己,我與我的同學都會視為一種幸運。雖然我的同學中有興趣教書的都未必能全部(入學)。當時我有去數間學校面試,而聖芳濟各是第一間錄用我的學校,甚至在與聖芳濟各簽約當日,有另一間學校願意錄用我。不過我比較喜款教中文,而那間中學願意聘任我為中文老師;但聖芳濟各則聘任我為社會科老師。相比之下我比較喜歡那間中學,當時我問那間中學的校長,希望早點知道結果,否則的話下午我便要往聖芳濟各簽約,但校長說他並不能作實,要等校董會通過。當晚那間學校打電話來,說明天可以簽約了,但可惜是今日下午我已簽了聖芳濟各。這件事也許可以說是一種緣份,因為通常是那間中學首先錄用自己就往那間中學簽約。
記:有否感到可惜?
徐太:也沒有。畢竟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,認識到朋友,工作也愉快。而且當時錄用我的另一間中學在荃灣,相對地比較遠。
記:教徒身份有否影響到入職聖芳濟各這個決定?
徐太:做老師與教徒身份關係不大,一方面這是我的興趣。我喜歡教書,甚至在中學階段已經諗過將來要投身那些行業,而教書是一個前列的選擇。正如我剛才說到,有學校願意聘請自己,便急於簽字,也沒有考慮是否教徒了。無論那間學校是那種宗教背景都好,能夠入職,在當時而言就能回饋家庭便足夠了。
記:對於老師這份職業,入職時有無想過成為終身職業?
徐太:係呀。我已當了是終身職業。好似”一入候門深似海”,都好難轉工了。而且工作也開心。
記:任教過那些科目? 這些科目中你最喜愛那一科?點解?
徐太:我的興趣在於教中文,但當時聖芳濟各在聘用我前已錄用了一位中文老師,因而校長希望我任教社會科、中史科及倫理科。任教初年都教這些科目為主,但這些科目始終並非我的興趣,例如任教社會科需要不斷留意社會的轉變,而且在往往末有課本下而要自備教材。這些都與我對中文、文學的興趣不同,漸漸校長也清楚我的意向,慢慢幫我轉營去教中文、中國文學、中國語文及文化科。因此除了初初幾年,我都是教中文為主。
記:經歷新舊兩校,你認為兩者最大的分別是甚麼?
徐太:當然是地點不同。學生背境都不同。校舍硬件方面,校舍比較大,設施亦比較好。我想這些都是時代的發展,時代的要求,而物質豐富,學校設施也也相對提升和完備化。
至於學生舊校學生比較懂得尊師重道;新校學生比較活潑、純品一點。石硤尾校舍好細,是官小模式。亦由於細,師生關係比較密切。而學生的背景往往來自九龍的屋村,與我的成長背境也很接近,我也是在屋村長大。大部份學生上進心比較強,對自我要求也高一點,所以當時不用花很大功夫便能教出成積好的學生;在粉嶺,學生家庭的支援相對少一點,往往需要花多點時間,例如補課、對個別同學作指導,對老師的依賴比較強。如果要在公開試上得到好成積,老師的付出會再大一點。

記:教學生涯中的難忘人/事?
徐太:教了這麼多年,時間如流水,不知流往那方向。較難忘的人方面,我相信是同事們,很多同事雖然離開了這間學校,但我們也有定時的聚會,大家也共事約廿年了,但感情仍然很好。
至於學生,總會有與自己投契的,他們間中也會探訪我,向我拜年,或者視我為朋友,邀請我出席婚宴、告訴我bb出世等,這種交往已不止是師生關係,而是朋友的感情。
又有一件難忘的事,發生在當年我任教社會科的時候。由於需要經常觀看教育電視,因而要將電視機推入課室,我也往往會挑選班中較”大隻”的同學去搬,但班中一位身型較細小的學生經常舉手,但很多次我也沒有選到他,原因是怕他太”細粒”而不勝負荷。因為這個搬的過情的兩個同學負責的,有一次這個同學又再舉手,嚷著要俾佢去搬,但可能是他們推得吃力,又可能他們在搬的同時又有嬉戲,結果弄翻了電視機,並壓住了這位矮小的同學。當時在課室聽到”隆”的一聲,發覺這個情況,便立刻通知校方,將這位同學送入醫院。我依稀記得這是放學前的一兩堂的時段,在發生意外後又見那位同學出現暈眩的現象,我當時很擔心,也不知如何與對方家長交待。因此由學生被送到醫院以至夜晚八時,我不停聯絡將這位同學送往醫院的工友了解情況。這晚對我而言實在漫長,尤其害怕如果這位學生的腦受到損害,影響的日後的生活與發展,我便會很內咎。所以這亦告誡我要選擇適當的同學負責,減少意外的發生機會及減輕憂慮。這件事對我實在猶有餘悸,幸好這位同學無恙,令我放下心頭大石,解放了這個憂慮我就去食晚飯。當得悉這位同學無恙固然開心,我也不期然聯想起,因為當時我他剛誕下女兒,如果我的女兒出了意外,腦部受了損害,往後的日子都不知怎樣過,因次這種憂慮的感覺實在令我覺得惶恐。
記:面對教育種種改革,例如負擔行政工作日多,對教育理念本末倒至,你以甚麼宗旨去應變?
徐太:我覺得改革其實是潮流,是身不由己,而作為一個老師,我不能憑個人之力去改變。有時新例的推出,我也不期然去想,這種改變對學生而言是否有好處,如果是好的話,自己則盡力去配合。而且其實這些行政工作也是本份,如果未能完成也只會加重同事們的負擔。我也盡力去完成自己的本份,畢竟每人都有負責的工作,無論在教學或行政也如是,而唯有大家合作,整體運作才會好。不過我亦不斷提醒自己,在新措施的推出同時,這對學生而言是否有好處,如果是的話就盡量配合;不然則作出調整。
記:有否產生過氣餒等感覺?
徐太:氣餒感覺人人都有,畢竟世事豈如人意。問題是只能在工作岡位上面做好本份,如果因為氣餒而影響教學熱誠,令自己不再願意付出,這並不是負任的行為,也對學生不公平。氣餒過後就要重整旗鼓,因為這是我終身的工作,也是我收入來源的工作,因而我需要在工作中尋找樂趣,另一方面確保我經濟收入來源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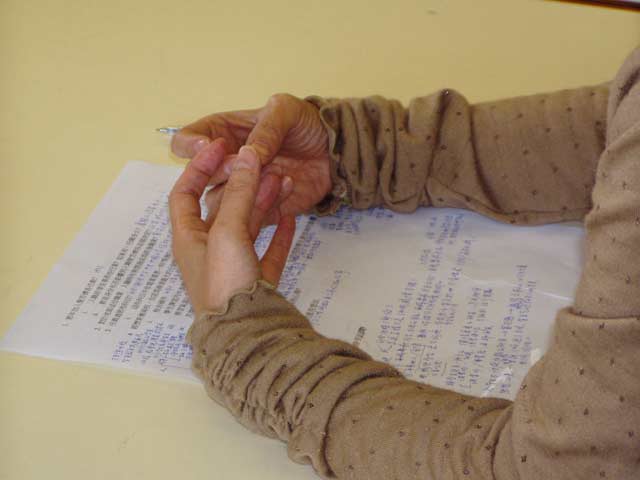
記:擔任德育組負責老師,有甚麼感想?
徐太:這個工作其實很有意義。生活教育牽涉的層面很闊,由價值觀到對人對事的看法,可能北區學生的家長支援不足,往往需要為口奔馳,未能騰出較多時間去教導子女,因此有些學生其實接受家庭教育並不足夠,在對話的過程中顯示出他們並未能有禮貌地,或洽當地與別人溝通,生活教育希望能夠針對這些情況。今年在早會制度中,由德育組五位老師輪流負責,並訂下在每個月有不同的主題,而早會則環繞這個主題,由老師、師生、多位學生等不同形式出作分享,透過不同的題材,不同的演譯,也會邀請德育組以外的老師去演講,希望學生能以多角度去思考。
記:面對現行教育制度對德育教育的不足,你認為對學生最致命的影響是甚麼?
徐太:為他們而言,讀書的重要的,而且未來例如入大學,也重視成績。但生活教育不足,令他們比較難以去建立一套正確的價值觀,可能管與教要相輔相乘。訓輔在於管;生活教育在於教,希望兩者合作能夠彌補到制度的不足。
記:對維繫學生的感情,有無有些心得?
徐太:維繫關係再於真誠,大家在生活上的見聞大家溝通、體諒和分享,這是友情建立的方法。
記:對教學的期望?
徐太:如果在教方面,首先我希望我的學生不會討厭我,層次高一點就是對我任教的科目有興趣,再高層次是就算他們離開了學校,也有興趣追求這方面的知識,同時亦希望不會因為我的任教而令學生在公開試貶值。
如果放遠一點不只在學業上,還有是心靈上,我希望學生可以在我的感染或教導下堅強一點,無論順境逆境,也要堅持樂觀一點去迎接將來,我亦希望他們的社會的弱勢社群施予同情。我想現在教書和以前不同,以前著重知識傳授,相對比較少去提及自己的感受,對人生觀的看法,現在在課堂外已比較少時間與學生溝通,因而課文如果能夠結合得到,我亦希望能從中帶出我對有關事情的見解,希望透過這些接觸,引起他們的共鳴,或能將我的價值觀帶給他們。希望在教與學兩者我都能平衡到。
記:其他補充/希望發表的意見想法?
徐太:關於中文科及文學科。中文科是比較工具性實用性的;文學是比較欣賞性。我比較喜歡文學,這科比較感性,亦固然因為我是中國人,文學可以說是對文化的承傳。而文學其實是文化的精粹,因為如果能夠將文學教得好,其實無疑是將中國文化最優秀的地方薪火相傳下去,亦令前人的知慧結晶不致失傳。而文學往往是以文言文寫作,而新的篇章傾向使用白話文,而如果我們對文言文將握得不好,我們的文化也會因此而失傳,因而我覺得文學有存在的意義。
而文學也能夠帶給同學比較闊的心靈境界。尤其在會考課程,如果分類為”人情””物理”的話,大部份也傾向於物理,而傾向於對客觀事實的研究如經濟、地理、化學、生物等都是對知識掌握的研究。但講到人情的科目較少,文學比較主觀、浪漫、有豐富的人情味。學生在掌握知識的同時,亦希望能同時受到感性的薰陶。而讀文學亦能對個人對語文的修養提升,多讀詩詞散文,能強化透過文字表達感情思想的能力。而現在學生往往表達能力不足,在提出別人不瞭解自己的同時,其實亦有著自己表達能力不夠強的問題,亦反著詞匯不夠豐富,亦不擅於表達自己的感情。讀文學得多,表情表意能力較強,在日後面對工作的壓力,能夠多一種感性而消解壓力的方法,但遺憾的是,文學科不受社會重視。社會重視實用科目,例如大學撥款傾向於新興物流等,文學相對不受重視,在未來幾年後可能聖芳濟各再也沒有文學科,而甚至考試局也會取消文學科。作為文學老師,覺得遺憾之餘,也是社會發展的不平衡。
出名的數學家丘成桐教授,穫獎無數,更被譽為”五十歲以下最有影響力的科學家”之一,現在於中大任教。現在政府因撥款問題考慮中大與科大合拼,具體如其他大學數學系學生前往中大聽丘教授聽課,可見其地位之高。他有些說話也可以與大學分享:「大學生也應該讀一點文學。不單能增加其思考性,也能消除在學術及感情而產生的壓力,以減少自殺。」我覺得他作為數學家,理科出身但對文學有這種體會,我很欣賞他,可惜在香港有這種識見的人並不多。文學科將會消失,是一件可惜的事

記:課餘生活/興趣?
徐太:作為語文科老師,與其他語文科老時也一樣,課餘也要進行評改作業的工作,準備筆記,雖然離開了學校,但在家中仍然要花一段時間對著電腦或評改工作。但人畢竟不是機器,我也需要抒發工作的壓力。我也有我的興趣,我喜歡做運動,尤其是游水,因為在水中的感覺很美妙,好像被很溫柔地包圍而沒有促縛,曾經有十年的時間我每星期游水兩至三次,每次遊40分鐘。但由於耳膜發炎,我因而要被逼放低這種我最喜愛的運動;近兩年則跑步,每次圍繞所住的屋宛跑3-4個圈,減輕壓力同時亦吸收新鮮空氣,令自己身體好一點,工作生涯長一點;最近半年則學太極,太極也是中國文化精粹的部份,學習如何修練到平靜的心境,與自然融和相處。練太極、跑步、行山,如果在長假期則出外遊山玩水充電。
我也喜歡入廚,尤其喜歡弄些天然無添加的食物,例如豆漿、麵包、芝麻糊等。一方面是個人興趣,弄完又有得品嘗成果;另一方面也符合健康之道。
另外我也喜歡閱讀,包括報紙和書。書方面每日也抽一點時間閱讀,抒展同時亦暫時離開現實,投入作者的世界,也視為一種進修。
我也會與朋友聯絡傾談。不難發覺上述的活動都比較個人,相對靜態。傾談對象無論是否同業。如果是同業,就更能瞭解我的情況,明白我的牢騷,在牢騷過後回到工作又舒服一點。因而與良朋知己閒聊,是對個人心理健康的提升。

記:書本的類型偏向中文、文學?
徐太:我的書分怖在浴室、書房、睡房。幾本書的類型亦不一樣。睡房的是李天命系列的其中一本《從思考到思考之上》;在浴室那本是歷史故事,剛看完了豐臣秀吉,稍後可能看織田信長。這些都是翻譯的歷史故事,就像中國的三國演義一樣;在睡房的則是張建雄的《教子篇》、《管理篇》、《處世篇》等。書的範圍其實也分多元化,並非限於文學。
記:另外還有那些需要補充?
徐太:入行多年,對於沒完沒了的評改工作,其實也感到厭倦,也渴望快點退休。去做希望能夠多做寫自己想做的事,例如學習烹飪,做義工等。現時由於工作,實在抽不到時間去做,而且評改、行政等工作亦的確比我初出道時為多,但亦隨著年月過去,體力亦比過往為差,因而難以長時間持續工作。因而希望快點完成工作,能夠做喜歡做的事、遊山玩水、指點江山、學我喜歡學的事,這是我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期望。這也不算是我對退休生活的計劃,畢竟仲有漫長的工作,我還年輕嘛!而人總不能退休後才開始自己的興趣,現在就要開始自己的興趣,希望自己在晚年的生活能夠有意義一點,亦從中獲得樂趣。現在也是時候開始經營了。但雖然如此,每次踏入班房,面對不同的學生,都為我帶來滿足感,這也是支持我繼續工作的動力之一。
記:有無說話寄語我們的校友呢?
徐太:我相信很多學生也認識我,畢竟我已在聖芳濟各打滾廿六七年了。有些在社會上都各有成就,在社會上也有不同專業,希望事業發展同時,也不忘母校,多點參與校友會的活動。有時老師也會邀請舊生回來演講,希望你們能樂意一點,能在自己能力範圍內提供其意見、經驗。其實過去邀請舊生回來給師弟師妹演講分享,效果亦不俗,例如醫生、又或者成積比較突出的同學,這樣對師兄師姐與師弟師妹的關係也好一點,對學校的向心力也強一點。學校作為聯繫站,拉近兩者之間的距離。